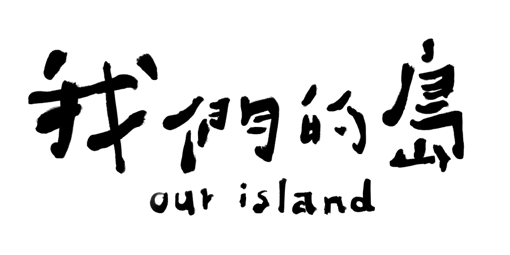狩獵是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生活重要的環節。對於許多原住民來說,山上的獵場是祖先留下的土地,上山打獵,就像是一條找回自己的路。當森林砍伐、棲地破壞、保育的壓力接踵而至,最直接衝擊到的就是在山林行走的原住民。流著獵人的血液原本是一種榮耀與驕傲,長久以來卻被污名化,打獵成為一件必須偷偷摸摸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觸犯國家公園法或野生動物保育法。
在原住民運動多年來不斷的爭取下,野生動物保育法在去年年初修正,增訂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原住民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的狩獵權終於被當成是原住民固有權利的一部分,獲得國家的尊重。基於這項修正,保育機關希望將原住民部落長久以來在檯面下進行的狩獵活動,搬上檯面合法化,開放狩獵的試辦方案也因而成形。


丹大地區是中央山脈的核心地帶,也是布農族人的傳統獵場。根據師大生物系教授王穎的調查,這裡野生動物一年的獵捕量超過五千隻,但是被抓到盜獵的案件,一年只有一件左右。規劃這次狩獵試辦活動的王穎認為,在強大的狩獵壓力下,丹大地區還能夠維持穩定的動物族群數量,這或許是一個機會,可以藉由開放合法狩獵,爭取當地原住民的認同,共同管理野生動物的資源。在同時,生物研究學術單位也可以藉由對獵物的測量、紀錄與採樣,建立丹大地區野生動物更完整的資料,做長期的生態監測。
布農族獵人領了「狩獵証」,拿著獵槍大方地入山打獵,可說是六十年來頭一遭。最引人注意的是,保育類的動物--水鹿、山羌、山羊等,第一次出現在狩獵名單上,獵捕的上限是山羌200隻 、長鬃山羊50隻、水鹿10頭以及飛鼠300隻,另外,每個獵人最多只能獵捕兩隻草食性動物及兩隻飛鼠。
行政部門對於狩獵時間、獵物等等的限制,與居民傳統的狩獵習慣,畢竟存在著落差。試辦期間的管理與限制,讓原本照習俗默默上山打獵的長老感到相當不習慣。另一方面,六十年來原住民第一次合法狩獵,吸引了許多媒體在檢查哨前守候。事實上,打獵對於部落居民來說本來就不是新鮮事,但是開放狩獵的消息對於媒體卻充滿吸引力,獵人一到了檢查哨便受到媒體的包圍。於是乎林務局這個將狩獵行為檯面化的動作,便意外地在媒體上渲染開來,林務局大概沒想到,開放狩獵對於媒體的意義,恐怕遠大於對當地原住民的意義。
林務局主動釋出善意,希望取得原住民的信任,但是獵人的反應卻似乎不如預期。行政部門不但要面臨來自原住民方面的疑慮,更受到保育團體的質疑。原本保育與狩獵之間的爭議,又再度浮上檯面。包括關懷生命協會等保育團體,連署要求農委會停止丹大地區狩獵試辦計畫。野生動物的生存權與原住民的狩獵權,何者優先?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再次交鋒。
價值觀的辯論或許會流於各說各話,但是,在政策的技術面上,野生動物的經營管理卻需要拿出科學、精確的數據,做為對話的根據。在民間團體舉辦的丹大狩獵討論會上,保育團體也提出要求,希望行政部門能有更完整的資訊。面對外界的質疑,王穎教授提出這幾年在丹大地區所做的「哺乳動物相對族群數量分析」。
指出跟四年前相比,水鹿、山羌等哺乳類類動物出現頻率呈現增加的情形。
開放狩獵試辦計畫的波瀾,凸顯了漢人社會與原住民部落之間的差異,以及行政部門與原住民部落之間長久的不信任。試辦計畫本身從善意出發,是否能達到善的結果,卻需要行政部門、學術單位、原住民與保育團體之間,更細緻的討論、更完善的溝通、以及更深刻的信任。
側記
部落裡年輕的獵人告訴我們,大溪上游沿線的野溪溫泉是水鹿最喜歡去泡水的地方,動物出沒頻繁,當地人稱「動物園」,吸引著我們前去。我們跟獵人過溪,走過孫海斷橋,在混濁的水流強勁的力道下,我們漸漸體認到為什麼老獵人總是不斷叮嚀,打獵就像是戰爭一樣,一定要遵守禁忌。
獵人與攝影師在冰冷的溪水中前進,一不小心三個人同時被大水沖走,幸好獵人經驗老到及時攀住岩石。一個晚上的成果是兩隻山羌,以及一台泡水的攝影機。本來帶著獵奇心情的我們,這時真正的感受到狩獵的過程,是一場嚴肅的生存遊戲,也是山林對人類最嚴苛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