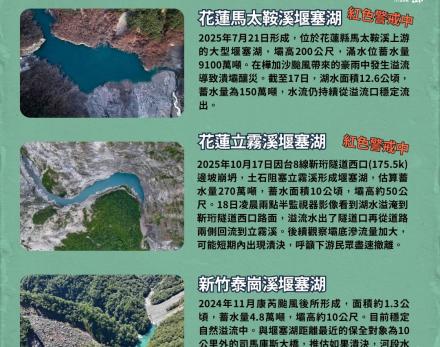生存:居住安全與中長期安置規劃

經歷過堰塞湖潰壩後,光復鄉的房子和家園,一夕之間都被摧毀,儘管泥沙已先清理乾淨,房屋結構安全和環境居住安全,仍充滿疑慮。
30歲出頭的蘇靖雯和高健盛,分別是高雄人和台北人,兩人為了夢想中的家園尋尋覓覓,最後決定在花蓮縣光復鄉落腳,選擇在佛祖街展開新生活,正在重新裝潢的牆上,隨處可見兩夫妻親筆劃下的記號,但是經歷泥沙沖刷掩埋後,牆面上剩下的只有一條又一條的裂痕。
高健盛說,我們最主要的訴求還是以安全為前提下去考慮,如果這邊確認是不安全、不適合居住的話,可能就只能遷村,除非在安全的前提下,這裡又可以恢復原狀,包含農田也能恢復耕種,不然就只能搬遷到適合大家生活的地方。

大同村佛祖街由於地勢低窪,是這次的重災區,儘管房子被泥沙掩蓋到一層樓高,只看得見屋頂,仍有居民捨不得自己的家,不願放棄。
佛祖街林女士表示,他們到現在都很難割捨對這裡的一份情,所以希望還是趕快恢復以前的樣貌,雖然有聽說要讓大家遷村,但是他們真的不喜歡,恐怕也不能同意遷村,遷村後回憶就沒有了。
同樣住在佛祖街上的Talo Yofo說,因為本身是原住民的關係,還是比較希望是留在原地,畢竟這是老人家留下來的地,捨不得離開,也不想放棄這塊地,希望堤防能盡量加高,然後穩固一點,颱風過後,淤泥就稍微挖一下,這樣會比較安心。
居民反映遲遲等不到中長期安置意願調查

對於中長期的安置規劃,居民意願各有不同,如果沒有第一步調查,難以形成符合需求的安置規劃。災後將近半個月,居民反映還沒等到政府機關前來詢問他們的意願。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處長陳建村對此回應,花蓮縣政府跟中央都已經分別跟各種專業技師協會,共同參與未來光復鄉中繼屋計畫的討論與評估,開始在聯繫並做意見交換。
房屋結構安全與環境居住安全引發疑慮

潰壩後的馬太鞍溪,地形、地貌已經改變,堰塞湖帶來的土砂堆積量有3億立方公尺,中游河道堆積達40到50公尺,下游的河道也淤高3到5公尺,這樣的居住環境是否安全,也讓居民相當憂心。
關於建築物的安全評估,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副署長於望聖表示,災害發生時,就已經有聯絡花蓮縣政府和花蓮縣的建築師公會,從10月7日開始針對目前縣府所提報出來,比較嚴重的89戶優先來處理,後續如果民眾個人覺得有需要政府來做房屋安全鑑定協助,可以去縣府或行政院一站式服務平台遞件。
至於光復鄉整體環境居住安全性的部分,陳建村指出,不管是花蓮縣政府跟中央都已經分別跟是建築、土木結構或者是水利相關的技師及協會,進行聯繫與意見交流。
Fata'an部落自救會提中繼屋需求,憂心族人被拆散

Fata'an部落自救會青年災後提出中繼屋的需求,原因是考慮到家園復原需要長期時間,部落需要集體中繼安置計畫,才能讓族人住在一起,並一起討論部落如何重建。

Fata'an部落青年、Fata'an部落自救會網路媒體組長Lisin Haluwey表示,最基本是離災不離鄉,中繼屋地點越近越好,老人家的心會比較安穩。地點之前有提過Karowa,也就是大農大富那邊,不過都還可以討論和評估,也要顧慮老人家的想法。對於中繼屋的想像,希望空間和建築樣式考慮到部落族人需求,讓大家可以先有一個安放心情的地方。
Fata'an部落青年、Fata'an部落自救會媒體聯絡人Kulas Umo表示,「關注過八八風災的情形,像永久屋這個議題,其實對部落傷害很大,所以我們不希望部落最後變成要住永久屋而且被拆散,也不希望在重建過程中,族人都只能被動接受,所以希望在重建的過程裡,部落能有自主權。」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盈豪提醒,應考慮原住民的文化,他指出,無論是中繼屋、避難屋或組合屋,選擇的地點需要有可以讓族人共同討論的空間,他們可能會很需要有一些廣場、空地或土地,需要與土地的連結,讓大家可以在這個空間有機的共同生活,透過部落和文化的方式進行療癒,討論未來大家希望重建家園的方向。
生計:600公頃農田遭600萬立方公尺泥沙掩埋

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導致花蓮縣光復鄉、壽豐鄉、萬榮鄉及鳳林鎮等地區的農田嚴重埋沒受損,農業部初步統計有高達600公頃、600萬立方公尺的農田泥沙量,有的土砂甚至淹到2公尺以上高度。農業部日前宣布針對這些鄉鎮的受損農地,補助每公頃10萬元。
光復農民卓彥華六年前決定回到家鄉務農,好不容易耕種硬質玉米的面積擴大到五甲,下定決心投資購買好幾百萬的機具,結果貸款還沒繳完,就被泥沙掩蓋。他說,這些土壤是沒有有機質的,是連砂石場都不要的廢土,它的密度太高,種任何東西都種不起來,施任何肥料都沒有用,只要一下雨就會變得很紮實,「講白了,現在土地幾乎是荒了,如果沒有把這上面那層覆蓋的土挖掉的話,幾乎是沒辦法耕作。」

卓彥華說,如果沒辦法在補助方面加強,就希望政府可以協助恢復原狀,讓基本的生存可以維持下去。
「活不下去啦,真的活不下去了!」光復農民楊欽文也損失慘重,除了農地被泥沙掩埋,剛貸款購買的農機也被淹沒。他說貸款250萬元買了農機,才剛還兩期,大概30萬元,算了一下現在的補助方案,只能補到差不多一半的錢,現在也沒土地可以耕作,沒有收入,真的已經沒錢貸款再買農機。
光豐地區農會總幹事張明發說,這次跟一般風災比較不一樣,淤泥真的太多,很多東西是被掩埋,希望補助從寬從優,鼓勵農民,幫他們恢復生計。

黃盈豪副教授指出,對於這類社區型災難的災後重建,他認為要有一個中繼安置,不是只因為有住的需求,還有生計的需求,因為災難,有人被迫離農,雖然給了房子居住,但是他們的農田已經不能再耕作了,那生計怎麼辦?所以需要綜合考量,特別是要從生活重建來考量,不只是住宅而已。
生活:心理重建、生活重建、文化重建

談到災害發生那天,在地許多經歷過這場災害的居民情緒難以平復,災後隔天,花蓮臨床心理師公會配合衛生局在收容所開設安心小站,並由玉里醫院、榮總玉里分院,以及其他花蓮的臨床心理師前往輪班支援。
臨床心理師陳百越也進駐排班,他表示,有些可能原本是健康的人,但是因為真的受到太大的震撼,包括財產的損失和家人的失去,會出現所謂的災害或創傷的恐慌反應。還有另外一群人可能原本就有些身心上的問題,比如說原本就有憂鬱症或思覺失調症,當這樣一個瞬間變動,非常容易誘發疾病又有變動,所以希望第一時間就能發現並協助大家。
除了災害發生後提供的心理支持,學者建議長期的集體傷痛也需要關注。黃盈豪表示,類似這樣的重大災難,對一個族群來說,是族群的集體傷痛,要怎麼面對這樣子的傷痛和創傷,不只是原住民部落,還包括整個光復,大家如何一起度過這個災難,也是需要有一些集體的工作,去度過跟療癒。

核稿/廖婕妤,編輯/林彤恩、林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