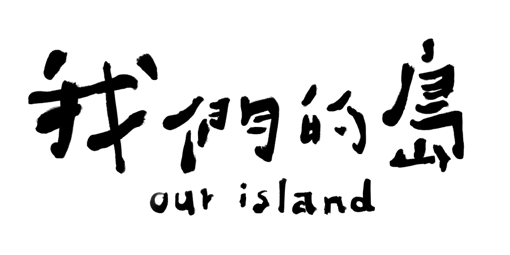寶藏巖社區位於新店溪南岸、觀音山丘陵南麓。康熙年間來台開墾的漢人在擊退泰雅族原住民之後,便在這裡興建“寶藏巖廟”,因地處水路要衝,逐漸發展成台北市南區的信仰中心。日據時期,日本人勘定新店溪為自來水水源,將寶藏巖劃入台北市的水源地,並且設立軍事碉堡。光復初期,日本人撤出,有部分居民進駐新店溪畔,靠著「鏟砂石」維生,在河岸興建砂石工寮,這些臨時搭建的工寮就成了寶藏巖最早的住戶。
光復之後,寶藏巖被軍方接管成為軍事重地。在層層嚴密的管制之下,營區內的外省老兵逐步突破禁建的防線,沿著山坡搭建起簡陋的房舍。民國六十年代,國防部警衛營撤離,福和橋也興建完成。在去除違建管制的壓力而交通更加便捷的雙重誘因之下,寶藏巖聚落在此時邁向了頂峰。一間又一間的磚瓦房櫛比鱗次地在小小的山丘上蔓延,從五六十戶最後擴張成為兩百多戶的違建住宅區。
這些操著四川、湖南、山東等外省口音的退伍老榮民,有些是原本就在國防部警衛營當兵,有一些是透過朋友的介紹而搬進這裡,除了這些外省老伯伯之外,更有許多在公館商圈擺地攤的中南部移民、在附近唸書的大學生,他們在這都市的角落共同打造了一個安身立命的窩。
民國六十九年,臺北市政府從消除地區髒亂的角度出發,將寶藏巖地區劃為公園用地,希望藉由公園的開闢一舉清除觀音山上的違建,從此居民也面臨家園隨時會被拆除的不確定命運。
弱勢居民安置的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寶藏巖的命運也一直懸而未決,這一拖就是二十年。台北市的變化日新月異,保存老聚落的新思維也在慢慢滋長。三年前一群由台大城鄉所學生組成的「寶藏巖工作團隊」,在寶藏巖展開長期的社區工作,並且持續遊說行政部門,希望將寶藏巖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歷史聚落」。最後這樣的想法終於獲得市府文化局的支持,將寶藏巖劃定為保存區。
將寶藏巖保存下來成為市政府、社區規劃團隊與社區居民的共識,但是該如何保存呢?民國九十二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展開了一個實驗性質極高的「寶藏巖全球藝術行動者參與計畫」,這項計畫打算將寶藏巖打造成全國第一個行動藝術實驗村,在今年三、四月推出了駐村藝術家的創作行動。在台灣,藝術家進入一個老舊聚落,與當地的居民共同生活,再以創作的方式傳遞對當地人事物的感受,這對於台灣的藝術家來說還是一個嶄新的挑戰。
正如市府文化局長廖咸浩所說,「通常我們對一個城市的想像,都是規劃得非常工整清楚、漂漂亮亮的,但其實城市的形成過程都不是這個樣子,有很多邊緣的、像暗影一樣的東西,可是這些被城市排除的東西,又黏著在城市的附近,這些往往是城市真正生命力表現的地方,刻劃了城市的深度與廣度。」
老兵、外籍新娘、大學生、社區工作者、藝術家.....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為了不同的目的來到了寶藏巖。他們在尋找什麼?
在文化局勾勒的「共生藝棧」願景下,寶藏巖彷彿成了台北市這棟擁擠的大房子裡,那閣樓上的一盞光。這或許是半世紀以來,棲身在都市角落的居民們始料未及的。而這一盞光似乎點亮了嘈雜都市中,人們想要追尋的那一點心中的寶藏。
側記
民國八十五年,甫從學校畢業的我剛開始從事新聞採訪工作,每天傍晚騎著摩托車經過公館後方那條堤外便道時,總會看到一幅奇妙的景象—在我頭頂上方是漆成鮮豔紫色的現代化高架道路,而旁邊是整片攀附在山坡上的破舊住宅,夕陽西下,天上的艷紫色對比著地上的老聚落,掩映著新店溪的粼粼波光。生長在台北城的我這才發覺,原來在喧擾的市區一角,也有這一方奇異的風景。
基於好奇心,也基於想找個便宜的租屋地段,走進了寶藏巖。當時寶藏巖還是公園預定地,還沒有任何規劃團隊或學生進駐,也尚未引起外界的重視。當時的我曾為寶藏巖寫了一篇「台北調景嶺」的文章,單純地想為這個地方留下一些見證。
時隔九年,寶藏巖還是寶藏巖,那樸實破舊的住宅仍然攀附在山坡上,沒有改變,但是,台北市改變了,人們看待城市的觀點、角度,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被認為是髒亂,搬不上檯面的角落,現在成為國際人士來參觀的地點,藝術家進駐的藝術村預定地,這不只是居民始料未及的,也是當年的我所無法想像的。
八年後,再度走進寶藏巖,撰寫它的故事,我驚訝的不再是寶藏巖的特殊,而是人的思維變化。當行政部門開始宣稱寶藏巖這個社區是台北市鄰里網絡的典範,我才強烈的感受到,我們所選擇的視角、看待世界的方式,真實地締造了這個城市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