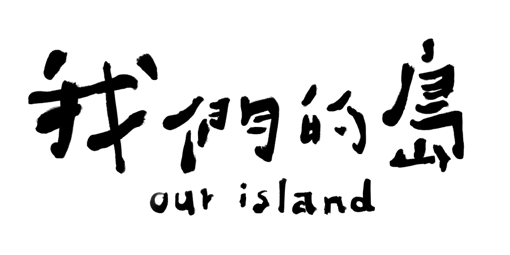俗稱癩病的痲瘋病,存在人類世紀很久,病患病發時,肢體五官殘缺,在早期醫學觀念尚未進步下,總是帶著恐懼與仇視的心理,以拘禁隔離方式對待。阿添叔十六歲入院,他一直記得與家人分離的時刻,在半路遇見爸媽的傷心。
在國民政府來台,依舊延續日本強制隔離政策,但是隨著新藥的研發,以及瞭解痲瘋病的低度傳染性,才陸續放鬆管制,直到1954年開放讓病癒的患者返家。官方的管制開放,但是並未有足夠的宣導教育,解開民間的歧視,樂生病患始終活在社會的排斥目光中。
社會的排擠,讓樂生院民走不出去,反而將這個曾經囚禁他們的場所,當成躲避歧視的家園,一住就是幾十年。痲瘋病正名為漢生病,世界開始注意迫害人權。樂生引發關注,許多醫療團隊,陸續進入樂生院研究調查,大專學生也會到院區陪伴老人。
從拘禁到關心,樂生院民在人間浮沉,原本想著以院為家,走完人生旅程,卻沒想到為了捷運興建,1994年將院區土地賣給捷運局,院民即將失去家園。因公共衛生被抓進來,又因公共建設被趕出去,樂生人總是沒有自己。
搬遷問題引發院民緊張,更讓關心樂生的人,擔心醫療與人權的問題。樂生療養院新建一棟醫院,前棟門診營業,後棟收容樂生院民,提供一個新的空間。但是樂生院民除重病者,需要住院治療,其餘院民生活都能自理,就像一般老人一般,只是需要關心,以及一個家園。
從關心樂生院民,到搶救古蹟老樹,樂生的議題,在早期並未受到太多的關注,甚至在開發的大思維下,淹沒一切聲音。2004年,青年樂生聯盟成立,結合一群關心醫療人權與文化生態的學生,開始搶救樂生。2005年,由樂生院民組成的樂生保留自救會,也開始為保留家園努力。
樂生的議題,在拆遷改建捷運機廠的背後,牽連著院民的醫療環境,以及台灣的文化保存,成為樂生運動的二大主軸。工程重新審議,不要迫遷院民,成為樂生運動的主要訴求,他們以跪拜苦行、絕食靜坐等等方式,到不同單位陳情抗爭,希望引發更多的關心。
為了讓更多人關心樂生議題,樂生青年為樂生老人製作音樂,透過歌唱的型式,傳達院民的心聲。莊育麟是黑手那卡西樂團成員,長期關懷台灣弱勢團體,為了樂生幾乎以院為家,成為新的樂生人。這群樂生青年,幾年來的堅持,有疲憊、有辛酸,但是為了理想,每個人不願放棄,放棄對院民的協助,放棄對正義的執著。
2005年底由文建會暫定樂生古蹟,並以六個月為期限,2006年台北縣市政府協商,完成保存百分之四十的方案,但是文建會委託專家協助,提出保留樂生院百分九十方案,卻在行政院以百分之四十原案備查,讓樂生失去保存機會。樂生青年與老人到行政院長官邸抗爭,希望引起社會關心樂生議題,但是警察的強勢驅離,讓學生氣憤,但是更寒心是媒體裡的報導,總是強調衝突,不談道理。
樂生運動的持續,引發更多外界的關心,專業者的加入,讓負責興建技術的捷運局,必須面對來自專業者的質疑。九成保留的方案,成為保留樂生與捷運通車的共存契機,讓樂生議題能有和諧結束的機會。彎距過大,始終成為不能保留樂生的言詞,但是捷運並非不能彎距過大,木柵線的九十度過彎,說明事在人為。眾多來自民間的聲音,在政府口頭關心之外,始終無法進入工程重審或古蹟審議的程序,讓樂生始終存在拆遷的危機。
從以往到現今,許多官員前來樂生關心,並且做出美麗承諾,但是面對開發思維,樂生立刻隱而不見,忘記所有誓言,對這樣的情景,樂生院民將無奈寫在歌裡。在不斷的陳情與抗爭之後,官員有承諾,但是無法落實。
一次次的街頭行動,學生們有著課業與家庭的壓力,但是從青澀到成熟,他們找到青春的不悔。張馨文是一位醫學院學生,社會定義下的菁英,但是她擱置學業,投入樂生運動,從早期的擔憂,到現今的無懼,在堅毅的行動裡,追求社會的正義。
對於院民們,這段學生相伴的時光,為著理想高聲吶喊,更是讓生命在悲傷中重生。幾年的奔波,老人與學生都累了,不只是四處抗爭的疲憊,更是面對強勢政府的心碎,一場晚會院民們說出心聲。學生與院民的情感,成為樂生最珍貴的註記,讓這個受到無情遺棄的人間邊境,添上溫暖的人性之光。有著學生的陪伴,院民的笑容說明一切,從不踏入樂生院的人,無法體會樂生家園裡,那種自然和樂的感受。
在網路等小眾媒體聲援下,樂生運動讓社會更多人關心,紛紛走進從未到過的樂生院,感嘆台灣還有這麼美麗的地方。拉扯、吶喊,樂生運動成為當今台灣最熱的社會議題,也許在模糊衝突畫面之後,該是靜下心,瞭解街上人民的心聲。
當新莊人走上街頭,以求生存、蓋捷運為由,要求拆掉樂生,讓努力的學生感到悲傷,樂生院民無奈岐視的歷史從未消失。對於處處水泥的新莊,讓捷運與古蹟共存,才是一個進步都市的遠景。四月十六日,樂生可能拆遷,當放棄所有可能解決之道,以強勢作為拆毀樂生,讓樂生的歷史,以悲傷為始、以橫暴為終,為台灣人權寫下遺憾的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