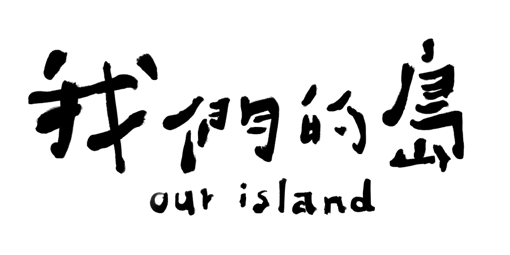1896年,林杞埔(今南投竹山)撫墾署署長齊藤音作組團欲攀登玉山主峰,卻誤登玉山東峰,隨行的林學博士本多靜六採集了第一份紅檜標本,將近八十年的台灣檜木砍伐史就此揭開序幕。1899年,阿里山作業所嘉義出張所書記石田常平,在阿里山發現一片由紅檜、扁柏組成的巨木林,歷經二十多年砍伐後,1935年日本政府在阿里山設置一座樹靈塔,有研究者指出,設置樹靈塔主因並非懼怕樹靈作祟,而更有可能是1934年日本訂定「全日本愛林日」、推行「愛林運動」的產物,附帶有強化國家認同及宣揚阿里山開發政績的目的,也無礙大東亞戰爭後期全面「徵召」原始林為國奉獻:
"我可以慰靈,但你得先為我而死"

民間圍繞著樹靈塔歷久不衰的靈異傳聞,固然存有部分批判殖民政府掠奪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或許也隱含了人類的愧疚之情。公視記者陳佳利長期關注盜伐議題,她提及2018年製作〈枉死之森〉專題報導時,前往新竹山區一處遭盜伐的香杉林,盜伐者的目的是取得號稱與牛樟芝有類似功效的香杉芝,被砍倒的巨大香杉屍橫遍野,迫使記者一行人只能以跪姿在樹身下爬行。陳佳利回憶,她爬過樹底下時心中湧現滿滿的歉意:「我是帶著懺悔完成那個專題的。而且我覺得樹會把祂的哀傷傳遞給進到那個領域的人,真的會。」近年香杉盜伐暫息,推測是因為林杰樑醫師在2013年根據一份經濟部委託的試驗報告,提出牛樟芝有安全性疑慮,但紅檜與扁柏等珍貴樹種的盜伐仍未停歇,甚至變本加厲形成集團犯罪。陳佳利感嘆,製作森林相關專題時,最辛苦的不是路途遙遠,而是看到過往的錯誤持續發生。
「台灣雖然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森林,但了解森林的人其實不多。」喜愛登山的陳佳利發現,即使是戶外活動的同好,也不見得清楚自己途經的山林發生了什麼事,或是過去森林保育運動的歷史。這便是「我們的島」製作《檜木林》這部紀錄片的初衷:希望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讓觀眾了解三十年來的森林保育運動脈絡。
生態人文學者陳玉峯在其著作《台灣植被誌(第四卷)檜木霧林帶》指出,「20世紀的台灣林業史,事實上就是伐檜史。」台灣森林保育運動也與檜木息息相關,1987年《人間》雜誌記者賴春標接連發表三篇專文,第一篇就是〈紅檜族群的輓歌─西林林道記事〉,促成第一波森林運動,1989年禁伐天然檜木林;第二波森林運動起自1991年,陳玉峯揭發林業試驗所六龜分所砍伐櫸木原始林,促使農委會於1992年宣布全面禁伐天然林;不過到了1998年興起的第三波森林運動,才算是真正普及的公民運動,起因為保育人士質疑退輔會於棲蘭山以枯立倒木整理之名行砍伐之實,這是《檜木林》所介紹的重點歷史之一。紀錄片結尾安排退輔會森林保育處總技師張明洵,說明森林在木材生產之外的遊憩價值、生態價值,十分具有歷史意義。
另一個紀錄片點出、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是原住民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過去保育人士認為,要確保棲蘭山僅存的原始檜木林不受摧殘,最有保障的方式就是設立國家公園,但以往國家公園完全排除人為利用的思維,使生活在其中的原住民處處受限,傳統生態知識無以為繼,即使搶救棲蘭運動的幾位領導者皆強調國家公園的設立須保障原住民權益,但在信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馬告國家公園最終並未成立。所幸政府與原住民之間仍持續摸索新的夥伴關係,從「我們的島」相關專題如〈馬告山風雲錄〉與〈檜木鄰〉,到柯金源導演的新作《神殿》,都可以看出變遷的軌跡。
搶救棲蘭運動喚起大眾對森林的關注,至今已過了三十個年頭,對於森林的種種生態系服務功能,不少人已經耳熟能詳,柯金源因此不斷思索,想找出一條新的、以哲學思考為出發點的觀看路徑。如同他在《我們的島:台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一書中透露:「想延伸視野、超越祂們外在的形體,貼近表現其生命循環、以千年尺度計的護生功德,才能超脫現世的觀點。」
《神殿》提出的大哉問之一是「人為什麼會對自然界的一切現象感覺到美?」柯金源想詮釋「因為生命同源,你只要用心體悟就可能互相感應。」《檜木林》談的是台灣山林百年來從開發到保育的歷史,《神殿》則藉由壯闊山景的鳥瞰畫面,傳達更加久遠的時間感。片頭之所以會有恆春出火特別景觀區及高雄泥火山的景象,是因為柯金源聯想到地球成形之初是個火球,之後才逐漸冷卻,因此想藉拍攝惡地形來隱喻四十六億年的地球演化史,藉由追溯共同的生命起源,邀請觀眾思考我們與巨木間的連結。
「時間」一直是各種民間信仰中生物甚至物品「成精」的要素。正如柯金源所說:「超過百歲的樹我們就會尊稱祂為老樹公,那何況在山裡面整片上千年的巨木,當你進入祂的領域時,不就像是進入神殿一樣嗎?」若是回到台灣森林開發史的脈絡,神靈的意象可以延伸出更多思辨:人們對森林遭砍伐的愧疚投射出「怨靈」的形象;大伐木時代終結後殘存的零星巨樹被視為「神木」,成為觀光景點,但學者早已發現孤立檜木容易枯死或被風吹倒,陳玉峯引述植物學者柳榗的形容:這些「神木」往往「寂寞而死」,即使以神為名,祂們與親族之間、與人類之間的聯繫早已斷絕。

根據《台灣植被誌》的記載,泰雅語稱紅檜為 Ka-pa-rong Ma-why,扁柏為Ka-pa-rong Ko-zit,兩者統稱「Ka-pa-rong烏‧杜」,烏‧杜不僅是神靈之意,也代表泰雅族人在自然中的行事規範。陳玉峯寫道:「當你違反山林的和諧,烏‧杜會讓你知道;當你一意孤行,你會得到詛咒,你打不到獵物,你收成不佳,你得不到健康與祝福,嚴重的話,甚至無法延續後代。你必須懺悔,同烏‧杜與山林和解,你必須以雞或動物之血,灑在大地上,做潔淨禮且誠心贖罪,烏‧杜也將諭知你,是否已接受你的告解,如此,你得重回神秘的懷抱,接受它的慰藉。」由此可看出泰雅族人與環境的關係是彼此相繫而非分離。也許單獨一棵巨樹便足以令人浮現敬拜之情,但祂們若有神力,也是鑲嵌於整體自然界。一棵樹活在森林中才能像個神,被砍下做成神像只是一塊死木;真正的珍寶是完整的檜木原始林,而不是檜木聚寶盆。

曾至台灣採集植物的日籍植物學者松田英二曾說:「所謂自然的研究,不是世人所認定的,木與草的研究,不是土與石的研究,也不是蛇與蚱蜢的研究。是透過這些,去感知、敬拜終極的萬物之主,也就是神的研究」,所謂植物採集「不過是為觀察更深奧的、廟堂宮殿上的『某種東西』的程序而已。」矛盾的是,包括為台灣杉命名的早田文藏在內,支持這些分類學者研究熱情的是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有用植物調查」,目的是殖民地的天然資源。自然史研究者吳永華所著的早田文藏傳記名為「台灣植物大命名時代」,隨之而來的則是林產大開發時代。有用植物調查固然支持了部分純粹的學術研究,但一種植物「有用」與否,往往決定了它的命運。

柯金源便是有感於人類或許太執著自身賦予萬物的價值觀,因而導致種種種問題(例如將「奇木」視為珍寶引發盜伐),因此在《神殿》開頭引用了《道德經》中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他認為這兩句經文代表人類尚未為萬物命名、賦予價值判斷的時代。我們認為某些樹是一級珍貴木,某些樹是一般的雜木,「但生命的最初是很純粹的,萬物都同等重要,在一個生命可以自由繁衍的情境下在地球生存。」
人為何會將巨樹或森林視為神靈般崇敬?也許部分原因是人類認為森林在「守護」自己。我們確實受惠於森林甚多,但也許這些巨靈並不為捍衛人類而存在。《道德經》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並不是指自然對萬物殘暴無情,而是指自然的運行無善無惡。自然萬物本身的內在價值,便值得我們抱持敬意。
陳玉峯在《台灣植被誌》中寫道,紅檜常生長在溪澗谷地,當祂迎來生命盡頭而倒下時,常形成天然橋梁,「因而紅檜又寓含著:『山與山之間的橋樑;人與人之間的橋樑』,象徵流暢的管道,代表人與人、人與地之間的交通。」這兩部紀錄片本身也像是一座橋梁,不僅能讓觀眾藉此一睹深山中的巨木身影,更重要的是藉由這座橋梁,我們或許能開始尋找如何對待山林的最佳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