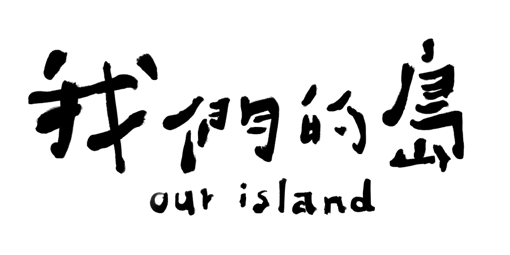民國69年,核廢料儲存場降臨蘭嶼,從此以後,伴隨著達悟小朋友長大的,有飛魚、迷你豬,還有核廢料桶。經過多年的反核運動,民國85年、91年,政府曾經先後承諾要將蘭嶼的核廢料場遷離,無奈的是核廢料遷來容易,想送走卻難如登天。
二十多年來,在蘭嶼露天的儲存槽裡,有數千桶核廢料因為海風與鹽分的侵蝕,而產生鏽蝕,另外有六百多桶有破損的情況,然而由於台電與達悟人長期以來僵持不下,不論是核廢料桶或是要換裝的空桶運到電光碼頭後,只能原船返回,也因此廢料桶檢整的作業始終難以進行。
核能發電所產生的廢料,包括高放射性的用過核燃料棒,以及放射性較低的輻射污染物質,如今在處理與運送上成為國際間一件尷尬的難題。根據198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訂定的巴塞爾公約,對國際間有害廢棄物的跨國境移動有著非常嚴格的規範,想要把自家不要的核廢料送到其他國家,挑起的將是世界性的反彈。
對於許多人來說,地方居民反核廢料的行動不過是「不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心理反射。誠如綠盟賴偉傑所言:「鄰避效應(NIMBY)在台灣已經被污名化為「還不就是想要多點回饋金」的代名詞,這樣的想法,使非鄰避者有了逃避「環境種族歧視」的藉口」(賴偉傑,感同身受與鄰避效應)。在這樣的解讀下,諸如「核廢料」這樣的「公共惡」被視為一種為公共利益而必然產生的結果,剩下的問題僅僅是究竟在誰家後院,價碼(補償金)多少。
然而,蘭嶼、台北縣金山、石門等地十多年來反核廢料的運動,終極儲存場地點難覓等等問題,卻突顯出一個事實:再多的補償金,再也無法收買民眾對於環境權的自覺。遷場時間遙遙無期、對於輻射的疑慮、對健康影響的恐懼,長期以來由於資訊的不透明與匱乏,居民缺乏參與的管道,在地方居民與台電/官方缺乏互信基礎的情況下,雙方永遠只能各說各話。
陽明大學醫學院教授張武修,長期以來投注於輻射傷害的醫療工作,在民國八十八年、八十九年間曾三度至蘭嶼,採集當地的土壤以及作物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在蘭嶼北方朗島附近的土壤與芋頭田中發現有人工核種銫-137的存在,他表示「像銫-137、鈷-60這些人工核種,這些絕對沒辦法排除說跟核電廠沒有關係。台電跟原委會必須進一步去了解,到底核電廠在這樣的運作之下,是不是有太多不應該的排放進入附近的社區。」
在蘭嶼反核廢料的運動暫告一段落之後,政府部門必須理解:「回饋金」絕對不是解決與面對核廢料處置困境的好方式,不論是輻射監測網的建立、資訊管道的建置與透明化、居民健康的調查研究、社區的重建,讓地方的居民能夠真正進入監測與決策的過程,才是面對核廢與核能風險的第一步。當這些經濟與社會成本被仔細估算之後,核能發電是不是一個值得發展的,就有待全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