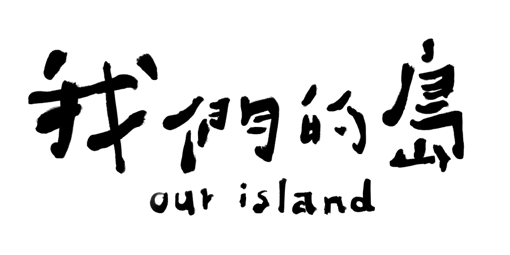每年中秋節以後,有一群特別的農人,臉上還來不及掛上秋收的喜悅,就又要下田工作了。田地旁的一處小角落,有三條二十多公尺長的白色紗龍,紗龍底下藏著,一片嬌柔翠綠的幼苗,不過將它放進嘴裡,卻是苦辣不已。它的名字,叫做菸草,收成經過加工調配後,就成為癮君子爭相追逐的對象。現在,在台灣,可是還有將近兩千戶的農家,在每年的秋天到隔年春天,都要靠它討生活。
假植,就是把長大的菸苗,一棵一棵種到穴盤內,這種方法,可以統一管理、控制品質、提高幼苗存活率,雖然會耗費更多人工,但是菸農們,還是想盡辦法互相合作、節省勞力成本。在高雄縣美濃鎮,這樣的勞力合作,叫做交工,到現在已經延續了一甲子。

【菸田裡的交工】
清除水井邊的雜草、把水排到菸田裡,七十多歲的菸農郭德傳,不斷地穿梭在水口和田頭之間。而剛種下的菸苗,在斜陽底下,正開始大口大口地喝水。郭德傳的次子郭富仁,也在田的另ㄧ頭顧水,對農民來說,農事似乎永遠忙不完,因為郭家田地裡的菸葉種好後,郭德傳隔天馬上就到張榮秀的菸田報到,幫忙種菸。
張榮秀的菸田,面積有七分大,一天之內,大家必須有效率地做完整地作畦,和打洞種菸的繁重工作。郭德傳、張榮秀、宋清光,是長期合作的交工夥伴。只要到了種菸的季節,他們就像一家人一樣,會共同把各自的農事,依序輪流完成。所有人一起勞動、一起生活。貨車變成餐桌,菸田旁的大樹下,自然而然成為菸農們的床舖。

在樹蔭下乘涼午睡,有人平躺、有人側躺。起伏的胸口、輕微的鼾聲,讓時光漸漸回到那段菸業的輝煌年代。遙想台灣菸草的發展,開始於日治時期。十九世紀末,日本政府引入日本種菸草在台灣試種,西元1913年,日本人更進一步推廣黃色種菸草,到了西元1939年,美濃平原上,開始出現廣大的菸田。
美濃菸葉大王林春雨,夥房堂號西河堂,家中曾擁有十座菸樓。他的孫子林明宏說,他的祖父跟美濃街長林恩貴,當年與日本政府談妥,引進菸葉種植進入美濃平原,開啟美濃菸葉發展的首頁。林春雨五子林華昌進一步解釋,他的父親有十個兒子,過去政府願意保價收購菸葉,包括他的父親,美濃鎮上人人都種菸種得很起勁,也種出興趣和成就感。
七十六歲的林華昌,不只擁有六甲的紅豆園,也是美濃鎮農會理事長。雖然他已經不再種菸,但是他們家的正廳裡,依然高掛著過去的榮耀。牆上,各種獎狀、感謝狀,說明了林華昌的父親-林春雨,當年對地方公共事務的高度參與,以及在菸業發展上的歷史地位。

香菸是一種嗜好品,香菸的原料-菸葉,是全世界栽培面積最廣的非糧食作物,也因此,菸葉被看做是「貴族植物」或「現金作物」。以民國七十四年為例,國產香菸銷售量近三百二十萬箱,也就是三百二十億支香菸,為當時國庫增加巨額收入。所以,無論是日治時期還是光復後,菸葉種植在台灣,一直都是專賣制度,生產、銷售,都由政府獨占。同時,菸農的身分背景、菸農家庭的資金成本,種菸的土地面積和栽培技術,以及燻煙的硬體設備,都必須合乎政府規定,才能夠獲得種菸的許可,而菸農辛苦的成果,政府也會以保障價格予以收購。


菸農為國庫賺進大把大把鈔票,政府採取兩手策略控制菸農生產,一是嚴格管理栽培,二是提供優渥利潤回饋農民。民國55年,一甲地生產的乾燥菸葉,年收入約四萬六千元,當時一位公務員的平均年薪,是兩萬六千元。民國65年,一甲地的菸葉收入是十三萬元,而公務員年薪約七萬八。這一年,同時是美濃菸葉發展的高峰期,種菸面積超過兩千公頃、菸農戶數一千八百戶,都居全台之冠,也佔全國的四分之一。
三面環山的地形、肥沃的土壤、四通八達的灌溉系統,是美濃種植菸草的環境優勢。傳統大家族的向心力、社區鄰里的交工制度,造就了美濃深厚的農業社會基礎。菸葉生產對美濃來說,已經不只是一項重要的產業,更是一種獨特的在地生活文化。

【菸農夜晚心事】
四十出頭的陳滿祥,出身菸業世家,家裡曾有九棟菸樓。今年他把上一季的菸葉屑末收藏起來,送給朋友朱秀文,拿來當驅蟲劑使用。
這幾年,陳滿祥的菸田裡,菸花開得特別多,不過菸花一開,就會影響菸葉的生長,這是所有菸農都知道的事。但是陳滿祥莫可奈何,如今的他,已經無心種菸,就算身為台灣菸業事業耕種改進社的屏東分社長,他也只能幽自己一默,直言菸業發展的末路。
他表示,身為分社長,是一個責任問題,可是卻沒有人替他想過。每個菸農年年都問,「可以種菸嗎?」、「有菸種嗎?」,分社長就有責任回答這些問題。如果政府不收購菸葉,分社長就會被罵、被責怪,甚至還被人說閒話,說是分社長把菸業搞壞了,對陳滿祥來說,這種心情實在不好受。陳滿祥感嘆著,菸農就像乞丐,求一次種一次,年年這樣才有機會繼續種,在這樣的時代,菸農好像真的只能靠乞討維生!

然而,陳滿祥口中的時代,是什麼時代?民國五十八年,全台種菸面積11952公頃,是種菸面積最多的一年。民國七十六年,政府開放洋菸進口,五年後,菸葉面積急速萎縮到7442公頃。民國九十一年初,台灣加入WTO,同年年中,台灣菸酒公賣局改制為台灣菸酒公司,廢除專賣制度,兩年之內,台灣的菸葉面積,驟降到1112公頃。今年,菸葉種植面積,702公頃。面對國際菸商的競爭,台灣菸酒公司幾乎毫無招架之力,對他們來說,再繼續收購國產菸葉,只會讓菸酒公司的香煙銷售量,也跟著衰退下來。所以,這個時代,是政府保不住國產菸業的時代!
從日治時期父親留下的耕種契約,到光復後政府核發的許可證,張騰芳都一一保存得完好無缺。身為台灣省菸業事業耕種改進社,任期最長的總社長,張騰芳看過無數次菸田,見證過菸葉滿園的盛況。但是他的驕傲下,藏著更沉重的失落感。張騰芳強調,他人生最有力量的時期,就是台灣菸業發展的最高峰,他把他的精力全都投入在菸業了,但是看到現在零落的菸田想著過去,他剩下的,就是心痛了!
下田後,入夜,泡壺茶聊閒話,已經沒有人想問,明年要不要種菸了!說起種菸的往事,是互相取暖的最好藥方。

【菸樓餘溫】
經過35天,張榮秀的菸苗,已經長得跟人的腰部同高。他請來兩位工人,幫他下田培土,讓菸葉根系可以生長得更穩固。兩個月過去,宋清光夫妻倆人全副武裝,正在灑第三次的農藥。當菸花盛開,劉日鴻夫妻正忙著斷蕊、除芽、施用抑芽劑。一月底,採收菸葉的時候到了!從種植、採收到燻烤,只要是菸葉季節,整個美濃鎮,沒有一個人閒得下來。
今年美濃鎮種菸面積,只剩一百五十多公頃,不過還是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工人,出現在不同的菸田裡。在張榮秀的菸田裡,每個菸農順著葉柄,手腳俐落地往同一個方向採收,接著合力打包、扛菸包上車。採收完,所有人往張榮秀家集合,將新鮮的菸葉,送進烤菸室。烤菸室,俗稱菸樓,過去是從日本傳來的大阪式菸樓,內部約四坪大、底層四個地窗、屋頂有六扇天窗。民國六十年代,台灣引進新式的循環堆積乾燥機,並沿用至今。
循環堆積乾燥機最大的優點,是自動控溫、調節溼度和節省人力,但是舊式菸樓燻菸的香氣,和冬天裡暖熱的炭火,依然是美濃人美好的集體回憶。民國六十七年,美濃平原上,有1814棟菸樓,可是到了民國九十三年,菸樓剩下八百多棟,而且有一半,不是受到毀損,就是部分結構被拆除。

空間的意義,在於人的使用方式與態度,菸樓為菸農創造財富,也凝聚出人與人的親密關係,在菸業沒落的此時此刻,菸葉生產空間的保存與後續利用,該何去何從呢?
另外,美濃鎮共有八座菸葉輔導站,過去一座輔導站對應一個特定的菸葉生產區。目前只有龍山輔導站還堅守崗位,提供菸酒公司收購菸葉。而其他的七座輔導站,大都已經閒置不用,惟獨美濃菸葉輔導站,已經成為當地社團或居民,推動公共事務的重要場域。
福安輔導站內,雖然外觀老舊、天花板被颱風破壞,但是鄰近的居民,卻為它描繪出新生活的輪廓。當地人利用輔導站種菜、資源回收、存放農業資材,甚至舉辦社區活動,這處過去繳交菸業的地方,像是老樹長新芽一樣地,生氣蓬勃。窗影映在輔導站牆面上,有如悠悠歲月在晃眼之間,爬上了菸農年輕的臉龐,又落在泛黃的回憶裡。菸樓的頹圮、輔導站的徬徨,道盡美濃人內心對菸業的餘溫,也載明菸葉王國迫在眼前的考驗。美濃人想知道,產業沒落、空間消失,那麼依存產業與空間形成的生活模式、在地智慧,要如何走出下一步?

【菸農不種菸】
郭富雲,五十歲,是菸農郭德傳的長子。年輕時為了幫忙種菸而回到家鄉,現在,則因為菸業沒落而積極轉型。
郭富雲種胡瓜,已經累積七年經驗。站在胡瓜田裡,他為剛種下的瓜苗,插好一支支竹架,寬度均等、角度一致,郭富雲有如一位農村裡的裝置藝術家。可是,積極的學習、努力的耕種,卻不見得可以像種菸一樣,有一份保障穩定的收入。
不種菸的菸農,總是在想辦法,要如何在農村謀生。面對大環境的改變,有人單打獨鬥,有人選擇集體作戰。美濃鎮果樹產銷班第一班,民國八十一年成立,九十三年創立月光山木瓜品牌,更在九十五年獲得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他們的木瓜,已經成功打進日本市場,也吸引許多國外農業人員,前來學習觀摩。
產銷班的成功,絕非偶然,不過卻少有人發現,種植菸葉的交工制度,是這一班班員團結、收成質量穩定的重要基礎。在整好地的木瓜園裡,十幾位班員分工合作,有人鑽洞、有人搬錏管,也有年輕力壯的爬上梯子綁鋼線。

整齊的錏管,代表的是產銷班的同心協力。想當初六年前,交工隊剛起步的時候,沒有人會搭木瓜網,然而到了現在,每個人都變成搭網師傅,可以幫產銷班的木瓜,架出一座又一座安全溫暖的家。用竹篙撐網、牽繩子拉網,網子如果卡住了,再搬個梯子來幫忙。交工隊熟練的合作模式,讓過去菸葉種植的生產文化,踏實地長進木瓜園裡。
郭德傳的太太德傳伯姆、郭富雲的一雙兒女,把昨夜拿出來回潮的菸葉,慢慢從鐵夾上卸下,堆置在儲藏室裡。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溫暖的香氣。這股香氣是美濃的冬天滋味,也促使美濃作家鍾理和寫出菸樓裡的人生;在「菸樓」這篇短篇小說裡,鍾理和寫著「血液都流上了腦頂」「在我眼前蠢動著的人群擴大了輪廓」「相反地,人聲倒變小了。」這就是鍾理和心中的美濃菸農-蕭連發。鍾理和長子鍾鐵民詮釋父親的寫作人生,他認為文學跟菸葉一樣,不長在土地上,就沒有生命。

經過十年時光流轉,台灣菸業,即將走下曾經大鳴大放的舞台。許多人還記得,菸農的臉上,有辛苦揮汗後的自信與笑容,當年只要不怕辛苦、團隊合作,從事農業也可以賺錢。
耕耘機鏟平菸梗,初春的第一期稻作就要落秧,田地裡,又出現活力了。沒有政府積極的奧援,菸樓、菸葉輔導站,或許年華老去無人聞問,但還是有機會展現新氣象。菸農心事無人知,從不知所措、憤怒、無奈,到自謀出路、另闢戰場,也是可以打出一片天地。有誰想得到?交工文化的實質內涵,竟也如此的傳承下來!
美濃平原上的轉變,有如台灣菸業發展史的縮影,菸業的困境,更是台灣農業危機的狼煙。的確,菸葉變少了、菸樓的溫度不再,在向菸業告別的同時,可別忘記,菸農曾為台灣種出的國家財富和農業文化。

側記
從西元2007年九月拍攝到現在,我們也跟著菸農迷惘起來了。前台灣省菸葉耕種改進社社長張騰芳說:「想到菸葉,我就心痛,我這輩子最用力的時候,就是在菸業鼎盛的時期,現在,菸田那麼少、菸農那麼老,好像我的人生就這樣慢慢歸零!」但是誰願意如此認為呢?我們寧願相信,一定有一些新的力氣,正在不同的田野上慢慢醞釀著。現在,菸農的抗議吶喊不再、政治人物的保證也遲遲沒有出現,零落的菸田,無聲地鋪陳在平原上,迎風搖曳的菸葉靜靜地向我們告別,那鍾理和筆下曾經有的笑聲、喲喝聲,也不在田地上了,菸樓滿倉的畫面,正大步從真實生活中退出。如果說,人與土地的關係是建立在「用力」的程度上,那麼如何讓農民找到用力的目標,建立用力的驕傲,將是我們繼續觀察和記錄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