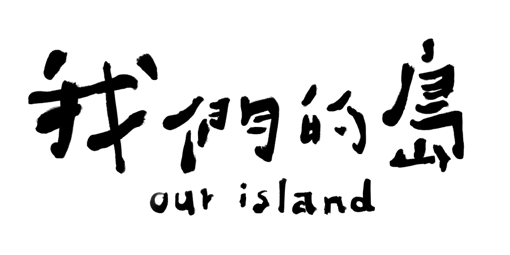我來到樹林,希望深刻地體驗生活,面對生命的本質,並從中學習它所要教我的事。我不希望到了生命結束時,才發現自己從未真正活過
~梭羅.湖濱散記
2005年我曾跟著促發森林保護運動的賴春標老師走進「扁柏神殿」,彼時台灣三次森林運動已經尾聲,民間團體抗爭結束,政策轉為全面不再侵擾天然林,馬告國家公園最終因為涉及原住民傳統領域而未能設立,賴老師的策略從抗爭轉為教育,希望延續培養一群保護珍貴天然林的種子。
跟著原住民獵人多次越過溪流、上下乾溝、山脊線,終於進入神殿的範圍。那次的經驗至今還像是夢境,仰望巨木森林,光線極少穿透,時間彷如靜止,似有古老的靈魂長居之境,言語難以形容的神聖感,可惜因為颱風成形,隊伍匆忙急撤,一直沒有再回去,一方面是這路線就算當時撒了麵包屑也無法再循跡而至,彷彿「南柯一夢」的樹洞入口已經關上,另方面不想再有人侵擾,只想讓神殿在心裡安住。一直到最近去日本屋久島巨木森林,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而那裡也歷經類似的大伐木到世界遺產保育的歷程。

進入「人類世」時代
世界上每個地方的森林都歷經了原始林、過度開發、逐步保育的歷程,大部分破壞與保育是循環發生,而更多地方森林已經完全消失,原始林因而相當珍貴,成為被謳歌、崇敬的壯麗存在。然而這種無人原始森林秘境的想像,並不存在,地球已經從「全新世」(Holocene)進入「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這種以最不易變動的岩層受到永久改變的跡證來做為地質年代的計時,往往以萬年計,科學家們從岩層發現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加速生產出來的新礦物或似礦物,包括在地層上堆積鋁、塑膠、混凝土,海灘上撿拾的石頭已經不是天然礦物,降雨裡面含有塑膠微粒、飛煙、放射性物質,如1951年核試驗的鈽已經進入地層沉積。甚至在地球孤懸八千萬年無人侵擾的紐西蘭,南北兩島演化出高度多樣特化的森林樣態,人們卻在紐西蘭以南約640公里的坎貝爾島上孤零零地長著的一棵北美雲杉的年輪層測得,放射性碳在1965年達到峰值,科學家傾向在這一年插入人類世地質年代起始的金釘子。

無人的自然已不存在,現世發生的災害也不再是天然災害。從汽車廢氣排放臭氧導致酸雨腐蝕樹葉;到為尋找替代能源而發展的生質能發電對燃料的需求,柴薪枝幹木料無法留在森林導致土壤貧瘠;或是人為引入外來種滿足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影響原生種;又或是因為野生動物保育、又缺乏大型獵食者,過量的草食動物對森林產生生長的影響……,這些人類行為與自然系統複雜的連動關係,已經不只是出發立意是否良善所能簡單判決的。當然維持原始林的保護範圍面積越大越好是重要的,而大部分時候,保育的訴求要能成功,往往希望連結人的生活,以喚醒人與自然的關係,比如日本的里山精神、聯合國的森林系生態服務價值等,不免引發諸如:懷舊式回到前現代生活或是現代舒適生活的替代方案、人類中心主義還是生態中心主義的保育論戰。擺在眼前的選擇,應該不是莎翁名劇裡「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而是面對各種人與非人行動者緊密交纏的複雜系統,進行對話、採取行動、試誤調適。
面對人類世的森林,我們仍會謳歌由時間凝結而成的巨木森林之美,同時看見漫長但非永恆的成住壞空,其中有母樹護衛哺育小樹苗的生生不息,但不會浪漫地以為森林僅是被我觀賞的對象。我們會感傷殘餘的巨株斷根,撫觸年輪、反思經濟利益的短視與皆伐的人為破壞,但不會絕對地以為「斧斤不入山林」是最佳的保育策略。我們學習到孟子說的「斧斤以時入山林」,雖然強調智慧善用,但不停留在「材木不可勝用也」的認知,或是簡化地測量年輕森林還是原始林何者固碳效果較佳,而是林木終歸並非僅為我所用。

走入森林,還要能「見樹又見林」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是要進入森林,讓人背離森林留在城市並不是保育,但要能「見樹又見林」。就像梭羅因為進入森林、簡單地生活,而發展出環境倫理的保育運動;解開樹的秘密語言的彼得•渥雷本,是因為在擔任林務人員時,規劃骨灰樹葬區才從客戶的眼光看到不同的樹木觀;而同樣擔任林務官的李奧帕德說:「對於何謂自然資源保護論者,我讀到過很多定義,自己也寫過不少相關的論述。但我認為最好的定義不是用筆,而是用斧頭寫出來的。定義涉及的內容是:人在砍樹或在決定砍什麼樹時,心裡所想的是什麼。自然資源保護論者應該是這樣的人,當他每次揮舞斧頭時,他都謙卑地知道,自己正在大地的面孔上留下簽名」。
就說「走入森林」這件事吧,走路的行為已經是相較於開馬路、騎乘車輛都更輕微影響的行為,但是踐踏會導致植被消失或改變、步道加寬、步道沖蝕、捷徑或複線化、土壤壓緊化,導致土壤中沒有空氣與水,樹木的根系無法獲得營養也無法向下扎根,步道會改變山體水的流動,變成路面逕流,減少地下水的補注,這是「路是人走出來的」後果;另一種可能是為了滿足人安全、便利、舒適、好走,下雨天不會弄髒弄濕鞋子的需求,而過度工程化的步道,為了搬運外來材料開闢施工便道,在施工過程機具挖填對自然生態與人文歷史的擾動破壞更大,而在自然裡設置更多設施物,導致後續維護管理更多問題。

最極端的當然就是所謂為了觀賞樹冠層的「天空步道」,步道本身傷害了自然而成為人造觀賞的短期目標。再說在山野裡「露營」這件事,已經比蓋別墅、山屋簡單,但人們想像的是在沒有森林保護、綠草如茵的山坡人造露營區裡,帶著所有城市生活的舒適泡泡移動,還是獨自在森林間、沒有其他健行者的樹下紮營,這兩者的想像都失之偏頗,前者的荒謬顯而易見,後者的程度有時候並未少於前者,因為當人們想像獨自一人做的美好的事情,實際上超量過度的遊客進入,衍生出便溺垃圾、飲用水汙染、植群退化,甚至變成商業化埋鍋造飯常態紮營,對森林生態系統與人們的體驗的影響仍然相當大。人們為了尋找無人森林的想像秘境,便不斷地向原始林擴張,而此種靜謐想像越發不可得。
人與自然共存共榮
人類世的時代,我們應該謹慎思索的,不該是「完全控制自然」或是「完全不介入自然」,而是在兩者之間找到深刻而複雜的平衡。人和自然的關係,並不是一廂情願主張一棵樹都不要砍,森林就會恢復原始樣貌,而是面對人們生活的需求,應適度使用符合在地的方式經營。

智慧使用的關鍵字是「度」或說是「倫理」,度的衡量,需要理解系統的整體複雜關聯,智慧的基礎是科學的知識與物種換位思考的共感,而至今我還不確定自己是否拿捏得當智慧使用的度,隨著了解越多、經驗更多,戒慎的心情也越發強烈,因為每座森林都有獨特的環境生態系統,面對比人生命更長的尺度,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永遠保持謙卑之心去學習、去體會自然帶來的感受與氛圍,尋找減少對當地影響、符合當地生態的美學生活形式,採取適切的行動去修補。好比為了進入森林不減損生態,我們嘗試以手作步道的方式,讓大地的流水、樹根的生長維持原來的律動,學習在地文化先民的智慧行動,這裡面沒有神秘主義的魔法、也沒有立即見效的方案,永續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議題,而是時時刻刻的行動。
最後改寫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作為對自己與讀者的叩問,在人類世的時代,「不要問森林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對森林做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做為自然系統的一個成員,你可以為森林做什麼,能讓森林系統仍能持續對我們保有無私、無限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