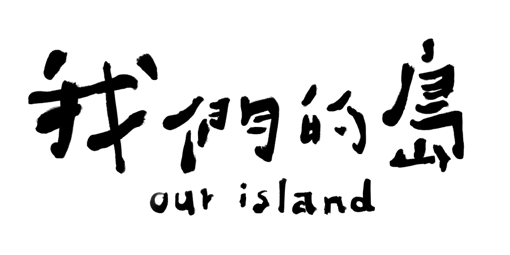我們與動物的距離,可以很近,也可以很遠。哈爾‧賀札格(Hal Herzog)在《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一書裡,提及研究人員發現人類大腦中有一個專門處理與動物有關資訊的區塊,對人臉或無生命物品都不會有反應。另一方面,人類活動已使數以百萬計的動植物滅絕或瀕臨滅絕,其中有許多甚至尚未被命名。
某方面來說,我們與動物的距離確實很近,或者該說與動物的「形象」或「符碼」很近。成語「葉公好龍」,說的是春秋時代一位姓葉的人非常喜歡龍,從衣飾到家中裝潢都充滿了龍的圖樣,天上的龍聽說這件事後,決定來拜訪這位狂熱粉絲,沒想到葉公見了真龍卻嚇昏了。
葉公對龍的態度,在現代社會中仍能找到許多相似點。以臺灣最普遍的動物符碼之一「十二生肖」來說,我們用它來算命,卻不見得關心這些動物的命運,甚至在牠們實際現身時,因厭惡或恐懼想除之而後快。《島嶼十二獸》系列短片的發想,便是希望人們能「看見」真實的動物。製作人于立平採取有別於新聞專題的呈現方式,降低資訊量,主要透過影像說話,給觀眾更多想像空間。十二獸雖然不全是臺灣特有種生物,但這些動物與臺灣互動的特殊脈絡,使這系列短片也被賦予了獨特的文化意義。

跳脫「純生態」紀錄,聚焦人與動物關係
一般生態紀錄片或許會將重點放在認識動物習性、傳遞相關知識,但我想《島嶼十二獸》所要傳達的,應該是人與動物關係的反思。
人與動物的關係最早只有一種,就是獵物與獵食者;約一萬四千年前,人類與犬科動物的同伴關係逐漸形成;畜牧起源於約一萬年前,隨著時代演進,又出現了役用動物、展演動物、寵物與實驗動物。奇妙的是,如今人類已經掌握幾乎所有動物的生殺大權,我們與動物的關係竟然沒有簡化成主人與奴隸,反而如同〈馬〉、〈狗〉、〈雞〉三部短片的導演劉啟稜所言,帶有某種愧疚感,於是人會援救浪犬、棄兔、為野生動物的生存而奔走,《島嶼十二獸》幾乎涵蓋了所有這些關係。
這系列短片中最親密的關係,當屬李開地導演的〈牛〉。他在金門老家的老耕牛與父親相伴將近四十年,透過一人一牛午睡畫面的並置,以及父親回想老牛曾經精力充沛,犁田甚至跟不上牠腳步的回憶,來訴說人牛之間的情感。鏡頭下的老牛不是犁田的工具,而是和父親一同老去的工作夥伴,一樣有想要偷閒不想工作的時刻,甚至連風濕的毛病也一樣。

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常常忘了自己也是一種動物。對劉啟稜導演來說,拍攝三種動物的過程就像是在照鏡子,看見人與動物都有的身不由己。不論是戰功彪炳的獵犬或賽馬場上的冠軍馬,都是因為牠們對人有價值而受到稱讚,這似乎反映了自己在職業生涯中,為了生活拍攝過許多形形色色的商業片或廣告片,即使受到肯定,卻不見得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這次《島嶼十二獸》在策畫上希望呈現多元性,讓導演們自由發揮的做法,讓他得以採取不同的表現方式。
「拿攝影機的人是非常獨裁的,我想要降低自己的『威權』,以純粹紀錄者的角色,去呈現這些動物當下的處境。」劉啟稜說。觀眾會在他所拍攝的三部短片中,看到動物們截然不同的生存型態、生活方式:擔任騎警隊坐騎意氣風發的馬、一身是傷被安養機構收容的馬、被主人用湯匙餵雞肉的寵物犬、獵犬與浪犬、格子籠蛋雞與在農田討生活的環頸雉。導演選擇的拍攝對象固然會透露某些價值觀,「但我並不是想藉此告訴大家一定要怎麼樣。」不論是要喚起觀眾某些情緒或掏錢購買商品,劉啟稜認為自己很常拍攝被他視為目的性強烈的片子,「所以我不想連紀錄片都這樣拍。」也正因為如此,他刻意剪了一段母女間的對話:女兒認為讓環頸雉吃一點農作物還可以接受,媽媽卻說「我們也要吃飯呀。」

是要不離不棄,還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我們與動物的距離該如何拿捏?這個問題有些時候並沒有「一定要怎樣」的標準答案。養寵物兔一定得不離不棄,但若是獼猴等野生動物,最好還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島嶼十二獸》系列拋出來的問題,不只是「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還有「為什麼某些兔子是寵物,某些是食物?」「為什麼要把動物當成寵物?」像嬰兒般被照顧、捧在掌心上,或者看似自由卻有一餐沒一餐,哪一種才是理想的「狗生」?劉啟稜打個問號。〈鼠〉的導演顏子惟認為,跟不能自由交配繁殖的寵物鼠、生活環境受到精心調控卻終身活在鞋盒大小空間的實驗鼠相比,溝鼠活的最健康。拍攝〈蛇〉的窩們工作室成員之一周麗鈞,曾猶豫片中關於球蟒的片段,是否助長了自己並不那麼認同的、把動物當成寵物的風氣?但最後她仍透過飼主對球蟒之美的訴說,打破「蛇很可怕」的刻板印象。

人是否一定要透過餵食或擁有,才能與動物建立關係呢?〈龍〉的導演周文欽,以生活在小琉球海域的黑環海龍作為龍這種生肖的代表,由於不確定是否能拍到足夠的海龍畫面,他原本的腳本中還加入了小琉球因觀光業過度開發帶來的廢水問題、海洋塑膠垃圾問題等,此外由於黑環海龍的尾巴和廟宇中的龍十分相似,也拍攝了廟宇的畫面來做對比,但由於最後拍攝到不少意料之外的精彩畫面,他決定捨棄所有與人相關的內容、剝除人類加諸在動物身上的符碼。周文欽說,拍攝野生動物時,並不是執著於非拍到什麼畫面就一定能拍到,「動物能感受到你是放鬆或處於緊張狀態,如果你放鬆的話,動物也會放鬆,給你的回饋往往超乎預期。」

人與野生動物的距離或許最遠,但這不表示我們無法建立某種形式的關係。周文欽的放鬆哲學是一種類型,執導〈虎〉的陳佳利與〈猴〉的導演陳添寶,都希望能夠設身處地從動物的角度看事情。〈虎〉片中幾個刻意將攝影機放低的鏡頭,是為了模擬石虎眼中的世界。陳添寶則說,獼猴咬兩口水果就隨地一丟的行為,可能讓農民深惡痛絕,但這在生態環境中有它的意義,因為能幫助植物傳播種子,被獼猴從樹上摘下、沒吃完的果實,讓山羌等其他動物也有機會享用。為另一種動物著想在動物界可是極不尋常的能力,獅子不大可能考慮被自己獵殺的羚羊的心情,或羚羊是否快要絕種。話說回來,正因人類對環境有著其他動物沒有的掌控力,發展這種能力是必然也必要的。

在不停變動的關係中,尋找更好的相處方式
《島嶼十二獸》的七組拍攝團隊各有其特色,若要說這系列影片是否有一個主軸,大概是人與動物間的關係不停在變動,而不同文化對動物的不同看法,也常使既有的界線變得模糊,或顛覆既有的刻板印象。周文欽之所以選擇拍攝蘭嶼的山羊,是因為牠們每隻耳朵都有擁有者做的記號,毫無疑問是家畜,卻又活得像野生動物,「原來家畜也可以活得自由自在」的想法吸引了他。
賴冠丞的拍攝對象是另一種在達悟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動物──蘭嶼小耳豬。他想把重點放在人豬關係的改變:原本作為財富象徵、獻祭海神牲禮的豬,在文化變遷下逸出野外,成了破壞農作物、被懸賞狩獵的野豬。


〈牛〉也是一個關係轉變的故事。過去農業社會少有吃牛肉的習慣,但2006年後金門縣政府為去化逐漸蓬勃的製酒業產生的酒糟,推動以酒糟飼養肉牛的計畫,如今酒糟牛已成了金門名產之一,而父親與老黃牛的情誼將消失在時代洪流中。
相較之下,有些改變則充滿希望。例如石虎、獼猴、環頸雉這些會取食家禽或作物的野生動物,有許多人正在進行各種嘗試,減少牠們與人類的衝突。在幾位導演的例子中,他們與動物的關係或看待動物的觀點,也因為《島嶼十二獸》的拍攝工作而改變了。
李開地因為小時候被自家老牛踢過,又離鄉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剛開始牛跟人都有些戒慎恐懼,後來牛見到他與父親說話,才逐漸放鬆警戒。李開地回想:「漸漸我們的距離越來越近,拍攝時牠也可以很自在地做牠平常在做的事。」顏子惟原本對溝鼠沒什麼好感,「但透過鏡頭近距離看牠們時,卻發現牠們的動作跟寵物鼠一樣,覺得有點可愛。」他進一步反思,溝鼠的存在也是因為人類製造髒亂環境,不管是可愛的寵物鼠或骯髒的溝鼠,都是由人的角度去詮釋的。
顏子惟坦言,現在在路上看到溝鼠還是會有不悅的感覺,縱使察覺到身為人的偏見,仍無法一夕消除。不過對照短片中穿插幾十年前的黑白滅鼠宣導片,再到2015年考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停辦農地滅鼠週,我們似乎有保持樂觀的理由。這系列短片可能會留下許多問號,但這些疑惑與自我懷疑,也可能成為改變的契機。